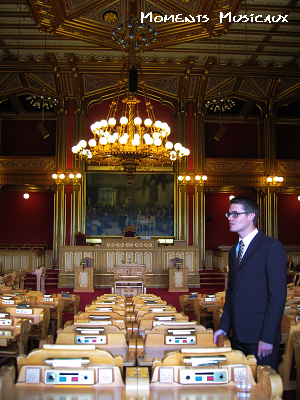【聯合報╱張大春】 2008.08.13 03:18 am
有些語言,用一用就死了,大抵說來,這些死得快的語詞、語句之所以早夭、天不永年,都是因為這語詞、語句所代表的意義被人厭棄。比方說我們讀古書偶爾還會讀到「咄咄書空」這樣一個詞,它源出於《世說新語‧黜免》,本指中軍殷浩被廢,終日臨空作書,寫的也是一個「空」字,被旁人看去了,說這真是「咄咄怪事」,於是引用的把「咄咄」和「書空」連起來,就成了自嘆無奈的意思。我敢斷言:這個詞遲早是要死的。即便是現在,這四字成語就算還沒死,也去了大半條命。為甚麼呢?不是今人沒有感傷無奈的情緒,而是感傷無奈不會用向空寫字來表達──這個成語之所以過時,其實是它最表層的意義消失了──今天的人大抵不寫字了。
「時醫」,也是這樣一個語詞。今天有任何醫事糾紛,醫生永遠是對的,怎麼可能有一種人永遠是對的呢?我想這跟絕大部分的人對某一個專業沒有檢驗或監督的知識有關。病家死活沒有本事對付疾病、也沒有能力瞭解整治那疾病的人,就不會徹底質疑醫生的權威,甚至不敢不信仰醫生的權威。在這種時代,就不會有所謂「時醫」這樣的詞,這樣的觀念。
「時醫」,命好運佳的醫生。
浙江嘉興縣西南有個檇李郡的醫生姓吳,人稱吳大夫。吳大夫自己業醫,家裡還開著藥鋪。有一回縣太爺的女兒感冒,請吳大夫診視,用了一味防風散。防風是藥草名,有美麗的羽狀複葉,葉片修長,開白色的小花,根可以入藥,有鎮痛、袪痰之效。防風散也是極為平常的一味藥劑。
縣太爺的千金服用了吳大夫的防風散之後,居然一命嗚呼,縣太爺二話不說,著即派人拿問。好在縣衙裡有吳大夫素來熟識的書吏,搶著派人先通知了,吳大夫聞風逃遁,到外省裡的岳父家避難去了。過了一年多,這一任縣令調遷他邑,他才敢攜眷回家來。
得以重新整理舊業,不是簡單的事,吳大夫的妻舅也隨同姊姊、姊夫一同回轉檇李,幫襯著要將醫局藥鋪重新開張。鄰里鄉黨在吳大夫出奔期間也覺得很費事,醫家一旦回來了,慶幸日後問診方便,大夥兒也都來慶賀,商訂某日集金募客,開宴招飲,大家慶慶團聚。
宴飲之夕,眾鄰里據案大嚼豪飲,忽然有叩門求痧子藥的。主人待客不得閒,遂囑咐小舅子說:「藥笥裡第幾格兒、第幾瓶兒,內盛紅色粉末者,便是痧子藥了。你去拿給人家罷。」那妻舅其實早就喝醉了,又是外省人,聽不明白吳大夫的囑咐,也懶得問,吳大夫說的是「藥笥」──也就是他隨身攜帶出入的藥囊──上下有隔層。可那妻舅聽成了「藥肆」──也就是隔壁的藥庫──茶几後頭再一尋,看見幾個紅瓶子,開來一看,還都是紅色的藥麵兒,隨手就撤了一瓶,發付來人。
宴客既畢,吳大夫回頭一收拾,發現藥房几上有個瓶子,登時嚇得酒醒了一半,忙問他妻舅:「這瓶『信石』怎麼會在這兒呢?」那妻舅一聽是「信石」,酒也嚇醒了,還兀自辯賴:「姊夫說是痧子藥,怎麼這會兒又說是『信石』了呢。」原來信石是砒石(俗稱砒礵)的一種,成粉末狀,有劇毒,以信州所產者為最佳,故稱「信石」。
「來求藥的是個甚麼樣的人?」吳大夫問道。
那妻舅想了半天才想起來,答道:「看模樣像是個行伍中人,穿著軍裝,拿了十幾文錢,我就給了他兩三錢的、兩三錢的──」「痧子藥」三字說不出口,「信石」二字更說不出口。
吳大夫聽罷嘆了口氣,道:「完了!我之不能得業者,恐怕也是命啊!明日一早,恐怕又要興大獄了,此身此家能否保全,我看都很難說呢!」此後,便祇有不斷地責怪小舅子。這做妻舅的祇好說:「還是趁夜逃走了罷──姊夫!一回生、二回熟不是?今番咱倆先走,留我姊姊在家聽風,要是一時沒甚麼緩急,興許也沒有大礙──這叫遠觀其變。」
無可如何,也祇能暫逃性命了。可這一回,鬧出來的事兒還不大一樣。原來病家是個權傾一方的軍事長官──提督大人。提督大人要痧子藥幹嘛?原來俗稱的痧子,有好幾種病。中醫一般把中暑、霍亂這一類的急性病都叫痧子,明代陳實功《外科正宗‧疔瘡》謂:「霍亂、絞腸痧及諸痰喘,並用薑湯磨服。」《醫宗金鑒‧幼科雜病心法要訣‧瘟瘢疹痧》云:「痧白疹紅如膚粟。」注云:「發於衛分則為殺,衛主氣,故色白如膚粟也。」衛分,是中醫行裡的名詞,所謂「營在脈中,衛在脈外,營周不休,五十而復大會。」
衛,有表面的意思。我懂不到皮毛上,怕有人聽了故事被我給醫死,所以祇能用清人俞正燮的《癸巳類稿‧持素脈篇》來做個小結:「衛氣者,初期胃氣之慓疾,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,而不休者也。」總而言之:這提督中夜起坐鬧肚子疼,而且腸胃攪動,如雷之鳴,四肢發軟,手腳端末之處不抓會癢,癢起來抓不著,提督自己判病,以為是發了痧,得了那信石,一口服下,不料立刻大叫:「妙藥!妙藥!」連問此藥從何而來?夫人告以出處,提督說:「這非當世良醫不可!一定要引來署中一見。」
到了第二天,提督手下中軍參將親自登門,也是個堂堂的三品大員了,率領一標人馬來家,奉上袍服冠履,白銀五十兩,往請吳大夫。卻發現藥局和門診都扃門上鎖,往來請鄰居地保出面,折騰了大半天,吳大夫那老婆才肯出見,瑟瑟縮縮問明來意,知道提督大帥並沒有教吳大夫給活活醫死,而且還有宿疾痊癒之勢。這才悄悄請人上路去把丈夫和弟弟追回來。
閒碎不多說,單表這吳大夫見了提督之後,一番望聞問切,還是不知道人家吃信石怎麼非但不死,還有栩栩然的靈動生機?祇好勉強應付了一回,說大將軍中了虛寒,得用參苓桂附為丸,慢慢調理,才得痊可。大將軍一高興,單憑這幾句話又賞了一百兩銀子。
可吳大夫畢竟是行裡人,得了賞錢不但不高興,反而愁眉深鎖,回家跟老婆說:「信石一服俱下,竟至於三錢,量大且急,居然還能治病?這真是天下大奇之事,必無常理,而不可再哉!你我要保全首領,要不是再逃一次,就得好生琢磨琢磨他這病情!」
吳大夫的老婆說得好:「為甚麼不問問大將軍身邊的長隨呢?人家天天跟著大將軍出入,飲食起居,鉅細靡遺,你詳加追問,一定能知悉緣故的。」
過了一段時日,吳大夫成天價同那提督府裡大將軍的貼身當差廝混,又喝酒、又嫖窯子帶賭錢,終於問出一個首尾。原來早年提督是以卒伍起家,青壯時還戍守過邊陲不毛之地,冬天沒有裘衣可以禦寒,早晚遇冷便以酒漿發汗催暖。北地荒寒野處之地,也不會有甚麼陳年佳釀,酒家為了讓飲者發汗,感覺身體得酒而自暖,還有一種祕方,就是拿少許的砒粉入釀,這還有個名堂,叫「霜葉紅於二月花」,故名「紅霜酒」。霜者,砒礵也。
後來大將軍發達了,開府南方,再也沒喝過這種劣等藥酒了,反而落了個不時鬧暈眩的毛病。這一次夜半起坐,夢中腹痛如絞,也吵嚷著頭暈。眾長隨都說不上來是因為甚麼──難道要提督大人再回邊關去鎮守鎮守嗎?
吳大夫一聽倒會了意,先前說藥師以參苓桂附等滋補之劑,雖說仍沿其舊,但是有了這一層病史的理解,吳大夫另外用信石作引子,製成一種丸藥,史傳上的記載是:「終一料而體竟霍然,疾不復發。大將軍深感之。凡所轄四營八哨九十餘汛屬下將弁,無論男女有疾,必使延吳先生。」可吳大夫的醫術究竟如何,記載上說:他要是把人家的病看好了,大將軍必然有重賞;看不好,大將軍就說:「連吳大夫都看不好他,那這病家的命數是盡了!」
有了大將軍這張保命符,吳大夫非但再也不用逃命,還一日一日發達起來、闊綽起來。沒幾年,就起了大宅第。吳大夫自書門聯一對,語云:「運退防風殺命/時來信石活人」。世人號曰:「時醫」,意思就是時運不到,甚麼人都得死在醫生手裡;時運一到,連死人都可以活過來看醫生。
【2008/08/13 聯合報】@ http://udn.com/
http://udn.com/NEWS/READING/X5/4468926.shtml